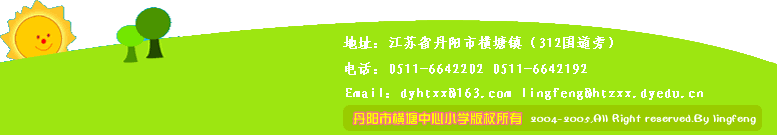|
坐在我镜前的我看着自己,一头短发,戴着一副眼镜,身材极其侵略性。倘若一个陌生人,面对我恐怕会有点不知所措,不要紧,只要说几句,你说会觉得我其实比较温柔,甚至可以称得上腼腆。
刚从学校下班回到家里,我拿了一杯啤酒,呷了一口,劳顿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在丹阳这样不紧不慢而又磨人的城市里,弄点啤酒不仅可以暂时摆脱生存的烦恼,感觉自己是这个喧嚣世界的局外人,而且被钢筋、水泥包围的身心在家狭小的空间还能放飞一回,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
在这样的时候,我似乎比平日更不关心同行们抛头露 面的欢呼雀跃。我知道我沉迷于基于个人体验的行为──创作方式。只要这种方式还没有逸出我的理想之外,我永远都不会轻易放弃。
话题,自然离不开画。读书时,我的油画系列很抢眼,而自我毕业之后,一直想致力于佛像体裁的开掘,从角度看,似乎更偏嗜于对抽象意味的追索,如果说在油画系列中我着力描绘的是远离工业文明的雅拙质朴的生存状态,那么,佛佗无疑寄寓了我对纯粹精神空间的向往。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每一件作品的色调都很沉静、敏感、简约。柔和的色调和色块的层层叠加,又折现出飘渺莫测的神秘韵味,看上去楚楚动人,不激不厉。倘佯在佛佗世界,一切外示的力量感与虚拟的气势皆被一一刊落,留下的是寂穆与冲淡。
从深层次上说,我钟情于佛国题材,这与我的个性也密切相关,我喜欢与三五好友闲聊,但更愿意独处。有时找些刺激,又有所节制,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却从不与人争执。在一些时候,我的内心甚至封闭或半封闭,而显得纤细而脆弱,这决定了我在文化选择与审美趋向上更容易指向纯净与恬淡。以荒率为高古,以粗陋为雄浑的流行主张,自然与我的绘画格格不入。也许我的绘画永远无法占据主流,不过,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心画”一词倒是可以骄傲地加在我身上。
奉献是美德。我自由地穿行于心灵的敏感地带,自由地心行于佛国仙境。
|